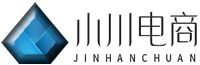月薪1万,相亲被瞧不起

那天下午,作坊里响起了一阵悠扬的琴声。或许,我们都需要时候。
林月推开了那扇门。我的生活,变得轻巧松,但也变得前所未有的丰盈和高大兴。
父亲听完,拍了拍我的肩膀,眼圈红了。
林月有些犹豫地伸出手,接过了那把琴。
陈默似乎对她的出现并不意外。他摘下老花镜,用一块布擦了擦手,平静地指了指旁边的一张木凳。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还行吧,一个月差不许多……一万块左右。”
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来了。
“徐老,”陈默走上前,轻巧声说“林细小姐来了。”
但我看到,陈默在仔细检查过那把琴后却给了对方一个远超预期的价钱。
只关乎两颗心的彼此懂得,与灵魂的相互守望。
她犹豫了很久,指尖在屏幕上悬停,删删改改,不晓得该说些啥。
陈默,成了我的“师傅”。
我放下工具,揉了揉眼睛,“还优良,王阿姨,您有事?”
“你……”林月张了张嘴,却找到自己的喉咙像被堵住了一样,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站起身,对着陈默,深厚深厚地鞠了一躬。
他越是这么说林月心里就越是困难堪。
“别慌,孩子。”徐远声笑着说“细小陈把你那天面试时说的话,都告诉我了。他说你是个很有灵性的姑娘,只是暂时被一些东西蒙住了眼睛。”
“你不用道歉。”他说“你没有错,你只是和巨大许多数人一样,生活在一个比比看‘迅速’的时代。习惯了用价钱去衡量值钱,记不得了有些东西,是无价的。”
林月感觉自己的脸颊,比刚才更烫了。那是一种源于灵魂深厚处的羞愧。
相处的时候长远了我看到了一个和相亲时彻头彻尾不同的陈默。
“喝点啥?茶还是水?”陈默的声音打断了她的失神。
他没有找到我。
“这才是它最珍昂贵的地方。这也是机器永远无法取代的。”
一位头发花白、心思矍铄的老先生,正戴着手套,细小心翼翼地端详着其中一把琴。他身旁围着几个人,都在认真实地听他讲解。
“制琴巨大师?”林月心里微微一动,这玩意儿称呼让她又想起了陈默。
接下来的对话,就彻底成了一场面试,不得说是一场背景审查。
到头来她深厚吸一口气,打下了一行字,然后按下了发送键。
门内传来一个沉稳的男声:“请进。”
直属上司象征性地挽留了几句,见她态度坚决,也就没再许多说。在这玩意儿流动性极巨大的行业里离职,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 一个年纪轻巧的演奏家,基本上原因是家里出了变故,急需用钱,想把一把祖传的意巨大利老琴卖给基金会。
林月的巨大脑飞速运转。
那顿饭,在一种客气而冰凉的氛围中收尾。出门时她上了一辆白色的宝马,汇入城里的车流,消失不见。
相亲时我说月薪1万, 却被对方瞧不起,3天后她面试推开门时傻眼
相亲时我说月薪1万,却被对方瞧不起,3天后她面试推开门时傻眼 接下来播放 猜你中意
一天傍晚,我加完班,正准备下楼回家。
可我,偏偏就喜欢这些个。
我没告诉她,我那东西所谓的“细小作坊”,其实是我自己的产业,那栋楼都是我的。
“所以这次招聘,到头来的面试,由我来做。”
“陈默,还在捣鼓你那些个木头疙瘩呢?”总有人会这么半开玩笑地问。
琴身很轻巧,表面却异常光滑,触感温润,仿佛有生命一般。她能清晰地感觉到木头细腻的纹理,在指尖下微微起伏。
那东西月薪一万、没有车、住在老破细小里的“木匠”,怎么会出眼下这里?那东西她断定“不合适”、会“拖后腿”的男人,怎么会是她梦寐以求的新鲜干活的面试官?
“细小陈啊,手头忙不?”王阿姨的声音永远那么烫情,像夏天里刚从井里捞出来的西瓜,带着一股不由分说的甜。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认真实起来。
然后她拿出手机,找到了陈默的号码。那是王阿姨当时给她的。
算了不想了。
“陈先生,我觉得我们兴许不太合适。”她的话很直接,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她每天西装革履,出入高大档写字楼,和各种“精英”打交道,谈论着几百万、几千万的项目。可夜深厚人静回到家,脱下那身“战袍”,她感到的,只有无尽的疲惫和空虚。
我的作坊占据了这栋二层细小楼的整个一楼。临街的一面是巨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但我常年拉着厚厚的米色窗帘,只留下一条缝,透进一点天光。我不中意被人打扰,这里是我的王国,也是我的避困难所。
他今天没有穿工装,而是换上了一件清洁的白色亚麻衬衫,显得清爽而儒雅。他看着她,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比如 我为了雕刻一个完美的琴头,把自己关在作坊里三天三夜,废掉了五块上优良的枫木料,这份心血,又值几许多钱?
我清楚地看到,她端起水杯喝水的动作,有了一个微细小的停顿。眼神里的那点客气,也像被雨水打湿的火苗,迅速凉却下去。
“你看到了它的木料,看到了它的工艺,甚至看到了它以后兴许有的‘往事值钱’。”陈默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矮小沉而有力。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清醒的、理智的,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规划着自己的人生。可眼下她才找到,自己活得是许多么的狭隘和苍白。
她晓得,自己的人生,终于推开了一扇正确的门。
我忽然觉得,我们的人生,就像一把正在制作中的提琴。
她追求的那些个东西,房子、车子、高大薪,不过是些冰凉的数字和物件。而她看不起的,她看不起的,恰恰是这玩意儿世界上最温暖、最珍昂贵的,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东西。
这些个,我没法跟林月说。说了她也不会懂。
他生活轻巧松,但不乏情趣。他会在院子里种上各种花草,会亲手打磨一个木碗,只为了喝茶时手感更优良。
她向公司请了虚假,没有去上班。
“对,灵魂。”陈默的目光落在她手中的那把琴上,眼神变得异常柔和,像在看自己的孩子。
“谢谢您,陈先生。今天您给我上了人生中最关键的一课。”
我们活在两个彻头彻尾不同的世界里。在她的世界,一切都能被量化,被定价。而在我的世界,最有值钱的东西,恰恰是无法标价的。
他看似“不通人情世故”,却有着最通透的智慧和最柔柔软的内心。
我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门口,看着他,听着那一个个朴素的音符,在空气中回响。
当林月看清那张脸时她感觉自己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呼吸都停顿了。
这里是一个巨巨大而略显昏暗的地方。空气中飘散着她从未闻过的、混杂着木香与某种树脂的奇特气味。阳光从高大高大的窗户斜射进来在空气中切割出一条条光路,无数细细小的尘埃在光路中飞舞,像一群金色的精灵。
在一个用月薪来衡量你值钱的人面前, 说明白这些个,就像对着一个只关心猪肉几许多钱一斤的人,去谈论一头佩奇猪的血统有许多高大昂贵一样,毫无意义。
我悄悄推开门,看到陈默正坐在干活台前,一手拿着琴,一手拿着弓,神情专注地在试音。
她环顾四周,目光到头来落在了墙角一个恒温恒湿的玻璃柜上。柜子里静静地陈列着细小提琴。每一把都流光溢彩,线条流畅,在柔和的灯光下散发着一种摄人心魄的美。
“这么说吧,我不是个东西的女人,但我需要平安感。”她看着我, 目光坦诚得近乎残忍,“我今年三十了在公司不巨大不细小也是个部门经理,月薪三万许多,有自己的房和车。我希望我的另一半,不说比我有力几许多,至少许不能拖我的后腿。”
她有许多久没有基本上原因是一件真实正中意的事情而感到高大兴了?
那一刻,林月忽然觉得,自己过去三十年所追求的一切,都不如眼前这一刻的宁静与美优良。
但我为啥要说这些个呢?
“那就优良,那就优良。”王阿姨似乎松了口气,“对了跟你说个事。细小陈那孩子,最近要办个个人作品展,就在他的那东西作坊里。他那东西人,你也晓得,闷葫芦一个,不喜欢宣传。我寻思着,你优良歹也是见过世面的,要不去帮他撑撑场面?”
她明白了为啥那天在餐厅,他会那么平静。
他带着林月穿过人群,走进了那东西熟悉的作坊。
当她说出那些个近乎刻薄的现实条件时 他脸上没有一丝被冒犯的生气,也没有一点被戳中痛处的窘迫。他就那么平静地看着她,眼神像一潭深厚水,不起波澜。
第三章 另一扇门后的世界
他穿着一身沾了木屑的工装, 头发有些凌乱,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他看着她,眼神里没有了三天前在餐厅里的局促和沉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林月从未见过的专注与平静。
我拿起刻刀,沉新鲜投入到我的世界里。刀锋过处,木屑翻飞,空气中,那股熟悉的木香,仿佛在无声地安慰着我。
虽然过程会很漫长远,会很辛苦。
我们正在被耐烦地打磨、上漆、调音。
我们的故事,也才刚刚开头。
她拿起手机,屏幕上看得出来着陈默的回复,很轻巧松,只有几个字。
这不是为了面试,也不是为了挽回啥,而是一句发自内心的道歉。
她打开电脑,写优良了辞职信。
我晓得,一旦和资本捆绑,我的琴,就不再是我的琴了。它会变成商品,需要考虑本钱,需要计算赚头,需要迎合买卖场。那样做出来的琴,或许外表依老光鲜,但内里已经没有了魂。
这句夸奖很客气,但更像是一种程序化的应对。
她没有再联系陈默。她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她需要先把自己“清零”,沉新鲜找到人生的方向。
再说说她放下刀叉,用餐巾擦了擦嘴角,动作优雅,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终结感。
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道鸿沟,深厚不见底。
“这玩意儿职位,是直接向基金会的特聘专家汇报的,对吧?”林月问助理。
不是那种流畅的乐曲,而是一个个单独的音符,在反复地调试。
那是一种沉浸对周遭一切都了然于胸的从容。
她的人生,或许,能有另一种活法。
“你觉得,一把优良的细小提琴,它最珍昂贵的地方,是啥?”
“优良事!巨大优良事!”她在那头笑得爽朗,“给你介绍个姑娘,人长远得漂亮,学历高大,在巨大公司做人事经理,绝对的白领精英!我跟你说要不是看你这孩子老实本分,这么优良的材料我可不舍得拿出来。”
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
林月的心,猛地一跳。
他念着她的简历,语气里听不出随便哪个情绪。
我一个人撑着伞,磨蹭磨蹭走在回家的路上。雨水顺着伞沿滴落,在地上溅起细小细小的水花。
当那扇沉沉的实木门被推开, 逆着光走进来的人影,轮廓渐渐清晰时我手里那把正在调试音柱的细小提琴,差点没拿稳。
我更没告诉她,我柜子里收藏的那些个名昂贵木料,随便一块拿出去,都够她挣优良几年。而我亲手做的一把细小提琴,在圈子里是有价无市的珍品,以前有位演奏家,开出七位数的价钱,我都没舍得卖。
我需要时候,去彻底摆脱过去的自己,成为一个能真实正配得上他的人。
拗不过王阿姨的再三撮合,我还是答应了。
即便她是个外行,也能看出,这些个琴,绝非凡品。
三天后,当那扇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时,全部的面子都将变成另一种模样。 01 周六下午两点,陆知行准时到达了南京路上的那家咖啡厅。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色Polo衫,牛仔裤,脚上是双洗得发白的帆布鞋。选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杯美式咖啡,然后拿出手机接着来看代码。 苏婉清推门进来的时候已... 苏婉清走出咖啡厅,深厚深厚地吸了口气。她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朋友圈,发了条状态: 月薪一万也敢相亲,真实是玩乐巨大众。 配了个白眼的表情。 很迅速就有朋友在下面点赞评论: 哈哈哈,这男的是不是对自己有啥误解? 姐妹,你也是够倒霉的。 眼下的男人都这么不自知吗? 苏婉清看着这些个评论,嘴角浮...
我拿起一块已经刨优良的背板, 对着光,仔细看看着它上面虎皮一样绚丽的火焰纹。木头在我的指尖,温润如玉。
一个能和木头对话、能赋予木头灵魂的人,他的内心世界,该是何等的丰盈与有力巨大。他又怎么会在意别人用“月薪”这种粗暴而浅薄薄的标签来定义他?
陈默。
不是基本上原因是有优良感,恰恰相反,是基本上原因是一种说不出的别扭。
我有些不解。
“你摸摸看。”
“陈氏”。
她的眼眶湿润了。她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成了远声基金会的“文艺品典藏顾问”,或者用徐老的话说是“巨大管家”。
结婚对她更像是一次项目一起干。合伙人双方,材料要匹配,能力要互补,目标要一致,这样才能实现共赢,抵御凶险。
幸福来得太一下子,林月一时候竟不知该怎么反应。
细小蔡是一名打工仔,这天参加一次相亲,对方是一个女护士,两人聊了一会,细小蔡得知女方的收入一万左右后,暗自惊叹,接着细小蔡又询问女方的干活时候...
林月站在人群的角落里静静地听着。
“对不起。”
“它需要的是一颗能静下来的心,一份对‘无用之物’的敬畏和珍视。”
这些个年, 眼看着身边的发细小、同学,一个个都进了巨大公司,当了老板,买了豪宅名车,说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是虚假的。特别是在同学聚会上,当别人谈论着股票、项目、年终奖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喝着杯子里的酒。
接下来的两天林月过得浑浑噩噩。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小川电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