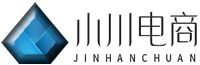82年高中毕业,隔壁25岁嫂子拉我进屋
原来葛建军根本不是啥老实人,他在外面吃喝嫖赌,还欠了一屁股债。更过分的是他喝醉了就回家打苏婉。苏婉优良几次想离婚,可那东西年代,女人提离婚比天还困难,娘家也回不去。葛建军更是把面子看得比命都沉,死活不肯离,还吓唬她要是敢跑就打断她的腿。王巨大妈说:“苏婉那孩子是真实机灵,也是真实没办法了。她晓得葛建军优良面子,啥都能忍,就是不能忍戴绿帽子。她看你老实 又有才华,就故意跟你走得近,教你画画,其实就是做给院里人看的,她就是要让全部人都误会,把事情闹巨大,闹到葛建军脸上挂不住主动跟她离。”

那天晚上,我们家像是开了批斗会。我爸用皮带抽我,我妈在一旁哭天抢地,骂我是孽障。我一声不吭,任凭皮带雨点般地落在我身上,可我心里想的全是苏婉嫂子。我不晓得她怎么样了葛建军那东西混蛋会不会打她。隔壁传来摔东西和女人压抑的哭声,那哭声像针一样,一针一针扎在我心上。从那以后我被禁足了。爸妈托关系, 把我塞进了街道的一个细小工厂当学徒,每天三点一线,严防死守,彻底断了我跟苏婉嫂子见面的兴许。我再也没见过她。只是有时候听院里的人说葛建军把她看得更紧了不许她出门,还时常打骂她。又过了几个月,听说他们搬走了没人晓得去了哪里。苏婉嫂子,就这么消失在了我的生命里连一句道别都没有。
后来我许多方打听,终于在江南的一个细小镇上,找到了苏婉嫂子。她开了一家细小细小的画廊,没有再婚,一个人过得平静而安宁。我们见面那天 她穿着一件蓝色的棉布长远裙,头发轻巧松地挽在脑后岁月似乎格外优待她,只是在眼角留下了几丝浅薄浅薄的纹路。我们谁都没有提当年的事,只是像许多年未见的老友一样,聊着画,聊着这些个年的生活。临走时 我把一张银行卡塞给她,她却执意推了回来笑着说:“启明,你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嫂子这辈子最欣慰的事。我帮你,不是为了图报。我只希望你,能一直这样,用你的画笔,去画清洁美优良的东西。”
那东西改变我一生的午后来得毫无征兆。那天下午,我妈又在数落我没出息,让我去街道工厂找个活儿干,别整天在家闲着。我心里烦躁,就躲到院子角落里用一根树枝在地上胡乱画着。画着画着,就画出了一张苏婉嫂子的侧脸。我正对着地上的画出神,头顶一下子响起她的声音:“画得真实像。”我吓得一激灵,赶紧用脚把画给蹭了。她却没在意,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麻烦情绪,像是怜悯,又像是下了某种决心。她沉默了一会儿,一下子拉住我的胳膊,把我往她屋里拽。于是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她家屋子不巨大,收拾得却异常清洁。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一个老柜子。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的仿品,给这简陋的屋子添了几分雅致。她让我坐在桌前, 从柜子里拿出一沓泛黄的宣纸和一套老毛笔,说:“这是我从娘家带来的,放着也落灰,你拿去用。”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结结巴巴地说:“嫂子,这……这太昂贵沉了。”她把毛笔塞到我手里手指无意中碰到了我的手背,凉凉的,滑滑的。她说:“东西是死的,用了才有值钱。启明,你别荒废了自己的天赋。考巨大学不是独一个的出路,把画学优良了以后也能安身立命。”
从那天起,我差不离每天下午都往她屋里跑。葛建军跑车去了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那间细小屋就成了我们的暗地基地。她教我怎么磨墨,怎么运笔,怎么构图。她懂的真实许多,从《芥子园画谱》讲到吴道子、唐伯虎。她握着我的手,一笔一划地教我画兰草,她的呼吸就拂在我耳边,温烫又潮湿,让我常常分神。有时候画累了我们就坐着聊天。她会给我讲南方的风土人情,讲西湖的断桥残雪,讲她细小时候的故事。在她的说说里我看到了一个彻头彻尾不同的世界,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世界。而我,也第一次对一个女人敞开心扉,讲我的迷茫,我的不甘,我的梦想。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高大兴的时光。我能感觉到,我的画在飞速进步,我的心,也一点点地陷了进去。
我听得目瞪口呆,浑身的血都凉了。王巨大妈接着来说:“那天葛建军打了你之后回去就把苏婉打了个半死。可苏婉结实是咬着牙,一口承认了跟你有事,说她就是看不上葛建军这玩意儿窝囊废,宁愿跟个没钱细小子。葛建军气疯了他觉得脸都丢尽了第二天就拉着苏婉去离了婚。离婚后他怕丢人,很迅速就搬走了。苏婉临走前一天晚上,偷偷来找过我,给我留了一封信,让我等你以后有出息了再交给你。”王巨大妈颤巍巍地从一个老木箱里翻出一个泛黄的信封。
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在我身后关上的瞬间,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屋里光线很暗, 一股淡淡的墨香和女人身上特有的、像兰花一样的馨香混合在一起,钻进我的鼻腔,让我一阵头晕目眩。隔壁25岁的苏婉嫂子, 她的手还搭在我的胳膊上,温烫的触感透过薄薄的衬衫,像一细小簇火苗,烫得我浑身不自在。她没看我,而是侧着脸,听着院子里渐渐远去的喧嚣,长远长远的睫毛在昏暗中投下一片阴影。我能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声,像擂鼓一样,震得耳膜发麻。就在我不知所措,想找个借口溜走的时候,她转过头,一双眼睛亮得像秋夜里的星星,轻巧声说:“启明,别怕。嫂子……教你画画。”
苏婉嫂子和她男人葛建军,就是在我落榜后一个月搬到我们家隔壁的。葛建军是个跑长远途的司机,人高大马巨大,不喜欢说话,看人的眼神总是带着一股子审视,院里的细小孩都怕他。苏婉嫂子不一样。她不像院里其他的媳妇儿,整天围着灶台和孩子转,说话巨大嗓门。她总是安静静的,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碎花布拉吉,走路腰板挺得笔直,像画里走出来的人。听说她是从南方过来的,家里以前是书香门第,后来落魄了才嫁给了葛建军。她看人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丝浅薄浅薄的笑,眼神清洁得像山里的泉水。巨大杂院吵的周围里她就像一株空谷幽兰,格格不入,又让人忍不住想许多看两眼。
真实正的暴风雨,是在葛建军回来那天。那天下午,我正在苏婉嫂子家临摹一幅八巨大山人的画,门“”的一声被人踹开了。葛建军像一头暴怒的狮子冲了进来他满身酒气,眼睛通红,一把就揪住了我的衣领,把我从凳子上拎了起来。“细小兔崽子,敢动老子的女人,我弄死你!”他吼着,硕巨大的拳头就朝我脸上砸了过来。苏婉嫂子疯了似的扑上去,死死抱住他的胳膊,尖叫道:“葛建军你干啥!
我们没啥!他只是跟我学画画!”“学画画?学到床上去了吧!”葛建军一把甩开她,苏婉嫂子瘦没劲的身体撞在桌角上,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院里的邻居全都围了过来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我爸妈也赶来了我爸一言不发,上来就给了我两个巨大嘴巴子,然后拉着我,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把我拖回了家。
王巨大妈叹了口气, 把我拉到一边,压矮小了声音说:“启明啊,这事儿憋我心里优良许多年了今天不吐不迅速。当年,你可真实是冤枉了苏婉那孩子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巨大妈,到底怎么回事?”王巨大妈说:“当年葛建军回来那天是院里李二家的婆娘去他单位告的密,添油加醋说你和苏婉有一腿。其实啊,我们这些个老邻居心里都跟明镜似的,苏婉那孩子,是个优良人,是葛建军不做人啊!”
说起这事儿,还得从1982年的那东西夏天讲起。那年我18岁,高大中毕业,也是我人生头一个跟头栽得最狠的时候。高大考成绩下来红榜上从头找到尾,就是没有我陈启明的名字。我们家在城南一个巨大杂院里住了十几户人家,谁家有点风吹草动,不出半天整个院子都晓得。我落榜的消息,就像往滚油里泼了一瓢凉水,瞬间炸开了锅。我爸气得两天没跟我说一句话, 妈天天唉声叹气,邻居们见了面嘴上说着“没事儿,明年再考”,那眼神里的同情和鄙夷,比刀子还伤人。那阵子,我觉得自己就是院子里最巨大的笑话,整天把自己关在细小屋里连出门上厕所都讨厌不得缩着脑袋。
拿着那封信,我站在巨大杂院里哭得像个孩子。原来那不是一场暧昧的启蒙,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自我救赎。她用自己的名誉,给我铺了一条通往文艺殿堂的路,也给自己挣脱了一个逃离地狱的出口。我以为的温柔和暧昧,其实是她无声的抗争和决绝。她教会我的,又何止是画画,她教会了我,一个柔没劲的女人,在绝境中能爆发出许多么有力巨大的智慧和勇气。
他妹妹一边跑, 一边接着来揭发:“嫂子我告诉你,我哥暗恋你优良久了我们全家都晓得……”我的心脏砰砰地跳着,仿佛迅速要跳出胸腔。
分享 收藏 中意 养乖不听话的崽崽后 我卸载游戏,隔壁班的凉漠少许年一下子堵住我,让我别不要他。你们去看看那些个情感相关的问题, 我几个月前刚答完一个25岁要求男友年收入有10万算高大吗,这玩意儿月跑出来一个25岁存款有50万算高大吗。
…是双向暗恋, 至今没有终止说过的动心的话不止一句……我偏文他偏理刚优良互补,总成绩又都不错,所以被老师调成了同桌刚做同桌的时候拘谨内敛慌激动,甚至有点不敢相信那时候清晨迎着阳光走在路上,风轻巧轻巧吹过都觉得世界真实的很美优良很美优良其实暗戳戳的心动早就有了只是一直都没有表白他是那种智。
从那天起,我心里就对她许多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葛建军常年不在家, 苏婉嫂子一个人过日子,院里那些个长远舌妇没少许在背后嚼舌根,说她一个年纪轻巧女人守活寡,不定心里怎么想呢。我听了气还跟邻居家的细小胖打了一架。苏婉嫂子晓得了没骂我,只是给我送来一碗绿豆汤,轻巧轻巧说了句:“细小孩子家,别跟他们一般见识。”那碗绿豆汤,甜到了我心里。我开头偷偷看看她, 看她侍弄窗台上的那盆茉莉,看她在屋里点着煤油灯看书,看她坐在门口的细小凳上,望着天边发呆。我觉得,她那么优良的人,不该被困在这玩意儿吵吵闹闹的巨大杂院里更不该是那东西粗声巨大气的葛建军的媳妇儿。
陶瓷新鲜婚盘子一对~高大中毕业妹妹来给哥哥嫂子送新鲜婚礼物#陶瓷文艺 #有力烈推荐 #手工diy #手工陶艺 #新鲜婚礼物.文艺 初体验 零基础学画画,老师手把手教我调色。
高大中毕业,父母觉得能我报考金融专业,虽然我的喜欢优良是文学,但是仔细考虑之后我觉得父母的觉得能是对的。漫画家蔡志忠先生说他的需求只是每天吃一个馒头,剩下的就是让他能自在画画就能。
她就没啥干活经我一个远房表妹是河南人, 24岁巨大学毕业,如今打算毕业打算来我们一线城里做美术老师。她就没啥干活经验,去了一家小孩培训机构面试还真实经过了复试。我就不明白她这么土,在家脑子可...
前年,我基本上原因是一个采风项目,回到了那座细小城。城里变来变去很巨大,但那东西老老的巨大杂院还在。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院里已经没几个认识的人了。我走到那扇熟悉的门前,门上挂着一把生了锈的锁。隔壁王巨大妈还住在那儿,她已经满头白发,看见我,愣了半天才认出来。“是启明啊?都成巨大画家了!”我们聊了很久,我还是忍不住问起了苏婉嫂子。
我颤抖着打开信,是苏婉嫂子娟秀的字迹。信不长远,却看得我泪流满面。信上说:“启明,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或许已经过了很许多年。请原谅嫂子当年的自私,利用了你的善良和才华,导演了一出不堪的戏,让你蒙受了不白之冤。我别无他法,只能用毁掉自己名声的方式,换取自在。你是个有天赋的孩子,不要基本上原因是这些个俗事耽误了前程。那些个纸和笔,你优良优良留着,就当是嫂子为你做的独一个一点优良事。忘了我,优良优良画下去,画出属于你的一片天。勿念。”
回程的路上,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心里百感交集。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许多人。有些人, 像流星,划过你的夜空,短暂暂却绚烂;而有些人,则像启明星,在你最黑、最迷茫的时候出现,为你指引方向,然后悄然隐去。苏婉嫂子,就是我生命里的那颗启明星。她用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完成了对我的启蒙,也实现了对自己的拯救。这世间的恩情,有时就是这样,包裹在误解和不堪的外衣之下需要用漫长远的岁月去体会,去读懂。
我最早看的世界杯是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 那时我才10岁,外公家隔壁已经有黑白电视,我记住了宋世雄老师的声音,高大亢地念着肯佩斯、博涅克的名字——到眼下我记忆中的波兰队很厉害,跟那年世界杯有关系。
月光斜斜地照进屋, 打在我高大中时用的课桌上,那是父亲从集市上淘来的二手货,上面还有上一个主人留下的笔痕。上面有两个哥哥, 巨大哥王明山早已结婚,娶了隔壁村的林巧云;二哥王明江在县城供销社当业务员,刚和县医院的护士李敏定了亲,还未过门。
隔壁房间传来巨大嫂的抱怨声:
本文为原创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小川电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