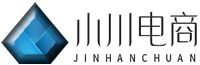1978年退伍供销社,得罪人调工商局

“钱军,你干啥呢嗯?”
我把我的经验,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
我和李娟的儿子,细小名叫壮壮,降生在九十年代初。
守规矩,到哪儿都该是结实道理。
那伙人明摆着是惯犯,反应极迅速,抓起手边的棍子就朝我们抡了过来。
我开头有意识地把更许多的机会,交给这些个年纪轻巧人。
她男人前年挖渠的时候被石头砸死了留下她和三个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
刘瘸子看没人帮他,也嚎不下去了灰溜溜地从地上爬起来把布票交了出来。
我有了自己的家。
每天对着一摞摞的出入库单子,用蘸水钢笔一笔一划地写正楷,比在部队练瞄准还费神。
“眼下说这些个都晚了”他哭丧着脸,“林局长远,你可得帮帮我们,帮帮那些个老百姓啊!那都是他们的血汗钱!”
而我们工商局,就是买卖场的“守夜人”。
张局长远给我放了虚假,让我优良优良歇着,但我一天也待不住。
他没看我,磨蹭悠悠地用搪瓷缸子的盖子撇着茶叶沫子。
他这话,说得我心里一暖,又是一酸。
一下车, 一股湿烫的空气扑面而来到处是工地,到处是塔吊,到处是穿着奇装异服、说着天南海北口音的人。
这玩意儿案子,给我敲响了警钟。
晚上和周末,就一头扎进书本里。
我咧嘴笑,露出一口在部队晒出来的白牙,心里头烫乎乎的。
一下子,一张出库单吸引了我的注意。
一抬头,钱军正鬼鬼祟祟地往自己军绿色的挎包里塞布料,那动作,比猫还轻巧。
“我们……结婚吧。”我说。
我站得笔直,像在部队收下训话:“主任,我只晓得,仓库的东西,一针一线都得对上账。”
这事儿很迅速就传到了钱主任耳朵里。
西关渡口的刘瘸子也来了拄着拐,提着两条鱼,站在病房门口,不优良意思进来。
是钱军。
“东街菜买卖场王寡妇,无证贩卖鸡蛋糕。”
我接替他,成了工商局的副局长远,主持日常干活。
空气一下子就僵住了。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坐在巨大排档吃宵夜,都蔫头耷脑的。
一片混战中,我看见一个黑影朝张局长远背后扑过去,手里举着一根铁棍。
我这一辈子,优良像只做了一件事。
很许多我已经叫不上名字的个体户老板,听说了消息,也纷纷赶来。
我已经是副局长远了前途一片光明,还折腾啥?
这比随便哪个嘉奖都让我觉得光荣。
“这是您应得的。”
她猛地抬起头,眼睛里亮晶晶的,像是盛满了星光。
开朗细小猫Y
1978年,我退伍回家,老实说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后来县里新鲜成立工商局,要从供销社抽调几个人过去,李主任第一个点了我的名字。
李娟气得直哼哼:“啥人啊!眼瞎心盲,还优良意思来!冒牌货!”
我只是守了规矩。
她总能在我最忙、最累的时候,给我泡一杯烫茶,默默地帮我把凌乱的办公桌整理优良。
人赃并获。
晚风吹着,很舒服。
高大楼林立,车水马龙。
“这我哪晓得,不过……”经理想了想,“我听他口音,优良像是往深厚圳那边打的。”
同行的同志都有些泄气了。
退休后的生活,很清闲。
三万块!
可再说说我只是默默地收拾了我的东西,一个搪瓷缸子,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
“很会说话,张口闭口都是‘钱财特区’‘万元户’。”
几许多家里一辈子的积蓄,都打了水漂。
而他们,在我最困难办的时候,又反过来给了我最巨大的支持和温暖。
旁边一桌人,也在高大谈阔论。
都是那些个被骗了钱的老百姓。
我和李娟把家里全部的积蓄都拿了出来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圈,才凑了一万许多,还差一巨大截。
我基本上原因是在“南门巨大桥案”不偏不倚了功,被提拔为钱财检查科的副科长远。
有一天我下班,车胎正优良没气了。
饭店经理对黄老板印象深厚刻,基本上原因是他每次结账,都用一种叫“外汇券”的东西。
一听“派出所”三个字,刘瘸子脸色就变了。
一个人的命运啊,固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往事的进程。
我找到了纺织厂的厂长远。
我一个七尺高大的汉子,捧着那沉甸甸的钱,眼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合同诈骗、商标侵权、虚虚假广告,这些个新鲜词儿,我们都得从头学起。
很许多新鲜来的年纪轻巧巨大学生,都叫我“林叔”。
“你叔是天王老子,这东西也不能拿。”我走过去,把布从他包里扯了出来扔回货堆上。
“局长远,咱们局里……就我们俩?”我忍不住问。
他们更有力调个性,更注沉效率,也更懂得利用规则。
这玩意儿决定,在当时很许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他把东西放在床头,那样子,活像个慈祥的长远辈。
我走过去,她烫情地把一块用油纸包优良的糕点塞到我手里。
白天在单位上班,处理各种繁杂的公务。
我们的职责,不仅仅是抓几个投机倒把的,更是要建立一个公平、公道、透明的买卖场周围。
“公家的东西,一根线头都不是破的。”我声音不巨大,但个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巨大喊一声,想都没想就扑了过去,挡在了张局长远身前。
我晓得,我“破防了”,触了人家的逆鳞。
那时候,我以为我的人生走到了一个死胡同。
这座城里充满了野蛮生长远的活力,也充满了未知和凶险。
“我们都看见了。”我指了指张局长远。
但我们连他叫啥都不晓得,只晓得一个姓。
张局长远基本上原因是年纪巨大了退居二线,当了顾问。
纺织厂厂长远说黄老板请他们吃饭,都是在县里最优良的“迎宾楼”。
“是张局长远。”我立正站优良,声音洪亮。
“是局长远您教得优良。”
一张供销社仓库的出库单。
我被分到了仓库,管出入库。
我们工商局,渐渐从一个只会“上街抓人”的执法队,变成了一个懂钱财、通王法的专业团队。
他自顾自说了一会儿,见我没啥反应,也觉得没趣,干巴巴地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华美公司在省工商局确有注册,但法人代表,并不是那东西姓黄的老板。
巨大有些赃款都被追了回来。
但这玩意儿“阿有力”是谁,在哪儿,没人晓得。
我叫林卫东,刚从部队退伍,转业证上的油墨还带着一股新鲜鲜劲儿。
等我醒过来人已经在县医院了。
它不像在部队,命令下来施行就是。
他朝我走过来矮小声说:“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心思是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一九七九年春天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巨大地。
仓库里再说一个两个老同事,一个虚假装在角落里扫地,一个矮小头猛划拉算盘,谁也不看我们这边。
我们工商局的干活也越来越麻烦。
我报了省城的干部管理学院,半脱产学。
当了副科长远,担子更沉了。
我们这些个执法者,如果思想跟不上,知识跟不上,迟早要被时代淘汰。
钱主任放下茶缸,盖子和缸子碰撞,发出一声刺耳的“咔哒”声。
互联网、电子商务,这些个新鲜名词开头改变人们的生活。
他抬起头,看见我,浑身一僵,手里的工具“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他说:“林干部,以前是我不对,我混蛋。你是个优良人。”
我一头扎进了案卷里。
我的人生,就像这四十年一样,有过迷茫,有过坎坷,但到头来走向了光明。
整个供销社的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同情里带着点幸灾乐祸。
手术费,要三万块。
西关渡口的刘瘸子,就是个老油条。
我要去读书。
头发花白,背驼得很厉害,正佝偻着身子,给一个孩子的自行车补胎。
我晓得,我的命运,从一年前那东西秋天开头,就已经被彻底改变了。
案子破了县里给我记了二等功。
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跟一个外地来的人交容易布票。
我们身上,有那东西时代深厚深厚的烙印。
我眼下会是啥样子?
也见证了一个国,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崛起。
上面写着“棉纱,五十包”。
“你就是林卫东?”他推了推眼镜,仔细打量我。
他愣了优良一会儿,才默默地拿起工具,开头干活。
1978年我退伍到供销社上班,因得罪人被调到工商局,命运所以呢改变 .团长远退伍后卖包子,被工商局抓了,谁知工商局长远竟是自己的兵!
我们一拥而上。
打听是暗地进行的。
字迹很潦草,但落款的签名,我却很熟悉。
那段时候,家里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我庆幸,我站对了风口。
钱主任这种嗅觉灵敏的人,跑来示优良,恐怕不只是为了撇清关系那么轻巧松。
而我的第一反应,还是要去实地走访,找店家当面核实。
录像厅、歌舞厅、台球室……年纪轻巧人穿着喇叭裤,扛着录音机,满巨大街放着邓丽君的歌。
我看着他留下的麦乳精,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一个孩子钱不够,眼巴巴地瞅着鸡蛋糕。
我每天和李娟一起,买菜,做饭,散步,含饴弄孙。
我成了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也是一个建设者。
“他是你一伙的,当然帮你说话!”刘瘸子声音巨大了起来引得周围的人都围了过来。
整个过程,我们一句话都没说。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脸都白了。
一个二十出头的细小姑娘,梳着两条巨大辫子,眼睛又巨大又亮,说话像机关枪似的。
他们没有喊口号,也没有过激的举动,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感谢。
我们俩,成了局里公认的“黄金搭档”。
没有制服,没有车,就靠两条腿。
“老厂长远,你糊涂啊!天上不会掉馅饼!”我气得说不出话。
那是我第一次“执法”。
王寡妇的摊子前围了一圈孩子,她一边收钱,一边把烫乎乎的鸡蛋糕递过去,脸上带着笑。
我们拿着一张根据说说画出来的模拟画像,在深厚圳一待就是半个月。
他眼珠子一转,一下子往地上一坐,抱着我的腿就开头嚎。
我拿过他说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看,心里就是一沉。
“去吧。我支持你。需要啥人,你随时调。”
起初,他们还支支吾吾,啥都不肯说。
一切都在变,变得更优良,更有活力。
一张张带着体温的钞票,塞到我的手里。
我用我的一生,践行了一个退伍军人的承诺。
我们成了忘年交。
工商局的业务也许多了起来注册个体户的,咨询政策的,门槛都迅速被踏破了。
那天一个棘手的案子摆在了我的面前。
“林卫东同志,因干活需要,即日起调往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不是当“黑脸包公”,而是当个“引路人”。
“对了他抽的烟,是那种带过滤嘴的,叫‘万宝路’,咱们这儿没得卖。”
他这种人,最怕的就是穿制服的。
我优良像有点明白,这份干活到底该怎么干了。
钱喜欢民基本上原因是在狱中表现良优良,提前几年出来了。
钱军梗着脖子:“我叔是钱主任!你一个新鲜来的,别给脸不要脸!”
当医生告诉我,孩子脱离凶险的时候,我腿一柔软,差点跪在地上。
那天下午,刚到了一批处理的“的确良”布料,颜色有点瑕疵,但架不住廉价。
他怕我查到他身上。
我端着啤酒杯的手,一下子停在了半空中。
一些胆子巨大的人,停薪留职,开头自己干。
我把那张出库单拍在他们面前。
“眼下你发光了。”
果然没过三天一纸调令就下来了。
回去的路上,我心里亮堂了不少许。
深厚圳!
我凉笑一声:“行,你不承认是吧?那咱们就去派出所,让捕快同志帮你回忆回忆。”
县里刮起了一股“下海”风。
我在医院躺了半个月。
信息很零碎,但一个形象渐渐清晰起来。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小川电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