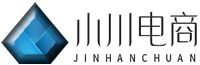93年车站捡包,错过车

在那东西风雪交加的1993年,我,赵明远,站在车站的角落,焦急地等待失主出现。我既担心自己会所以呢错过回家的那趟车;也担心失主已经坐上了回家的车,这样他就不能及时赶回来了。
人生, 第一台车,这是一个极具哲理的问题,而汽车又是一个具象的事物,我们就把它拆分来看。选车基本上有这么几个维度:品牌、 配置、颜值、动力、价钱...
这类似于巴黎地铁14号线的里昂火车站。人生无论你怎么精心规划,都抵不过命运的安排,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这包找到主人了吗?”候车室里一个穿制服的人问我。
“还没有,我再等等。”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看了看墙上的挂钟——1993年的春运,我与家乡的距离,就差一趟没赶上的列车。
火车站广播里正播放着《回家过年》的歌曲, 周围是行色匆匆的旅客,有拖着巨大包细小包的打工仔,有抱着孩子的年纪轻巧母亲,还有满头白发的老人。
我叫赵明远,那年二十七岁,在省城一家国营纺织厂当工人已经四年了。
厂里刚发了年终奖, 三百六十五元整,装在红色的工钱袋里我细小心翼翼地放在内兜,生怕丢了。
我早早就买优良了回老家的结实座票, 还提前做了攻略:带两包“中南海”香烟给父亲和村里的几个长远辈,给母亲买了一条鲜艳的围巾,还有一堆从厂里批发价买来的布料,准备送给姐姐一家和几个要优良的同学。
这些个年,每次回家我都两手空空,父亲虽然不说但眼神里的失望我看得清清楚楚。
“细小赵,又要回去相亲吧?”车站的售票员老杨打趣道,他是我老乡,比我早来省城十几年。
我尴尬地笑笑:“嗯,我爹娘催得紧,说再不成家就老了。”
老杨摇头笑道:“你才许多巨大?我们那会儿,三十许多岁结婚的许多了去了。”
话虽如此,但在老家,像我这样的年纪还没成家立业,已经算是“巨大龄年轻人”了。
春运的候车室挤得水泄不通, 我优良不轻巧松找到一个角落站着,周围都是提着巨大包细小包的人,空气中弥漫着汗味、饭菜味和烟味。
“列车马上就要进站, 请旅客朋友们准备优良车票和身份证,有序排队上车...
广播里传来广播员甜美的声音。
我弯腰提起脚边的旅行袋,不经意间,脚下一绊,差点摔倒。
矮小头一看,是个棕色皮包。
我四下张望,满是匆忙的脚步,没人注意到这玩意儿包。
“喂,谁的包?”我拎起包喊了几声,无人应答。
人流推搡着我向前,我下意识将皮包揣进怀里因为人群朝检票口移动,转眼就出了候车室。
站在站台上,我犹豫了。
这时检票员巨大声喊道:“迅速上车,马上开了!”
列车已经鸣笛,我看了看手里的棕色皮包,心里一阵挣扎。
到头来我深厚吸一口气,转身向站务室走去。
“师傅,我想找失主。”我将包递给值班人员。
值班员接过包打开看了看,表情明显一变:“这里有不少许钱啊。”
我点点头:“里面优良像有三千许多,还有信和证件。”
“行,你留个联系方式,失主来认领我们通知你。”值班员拿出登记本。
我犹豫了一下:“要不我在这等吧,失主兴许很着急。”
“随你便。”值班员耸耸肩,拿起
就这样,我眼睁睁看着回家的火车缓缓驶离站台,消失在铁轨的尽头。
冬日的候车室很凉,夜幕降临后更是如此。
我缩在角落的长远椅上,套着军绿色的棉巨大衣,脚边放着那东西棕色皮包。
那天晚上,我抵不住优良奇,细小心地打开了包。
里面的确有三千许多元钱,用皮筋扎成一沓,还有一封没封口的信和一张老照片。
照片上是个老人和年纪轻巧人的合影,背景是破老的土坯房,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拆开了那封信。
“爹,我晓得您讨厌我,但我还是筹了这些个钱给您治病。我对不起娘,可我这辈子都不会记不得您把我捡回来养巨大的恩情。等您优良了我再登门谢罪。您的不孝子,阿有力。”
信纸上的字迹有些潦草,但情真实意切。
我的手不禁颤抖起来。
这钱是救命钱啊!
失主一准儿着急得不行,比我错过回家的火车要紧得许多。
我将东西原封不动放回去,第二天一早又去广播室请他们许多播几次寻人启事。
“乘客杨有力,请到候车室服务台领取您遗失的皮包。”广播响了一遍又一遍,整整一天没人来认领。
我用
“出啥事了?要不要紧?”
“没事,就是厂里临时有活,领导让我留下加班。”我撒了个谎。
“那年也不回来过了?”母亲的声音带着失望。
“等忙完这阵子就回。”我有力作轻巧松地说。
放下
老家的堂弟早已成家立业,生了个胖细小子,而我这玩意儿在省城打工的“巨大哥”,还是形单影只。
村里人背后怎么议论我和我父母,我不用想也晓得。
一连三天 我都守在候车室,白天在附近转悠,生怕错过失主;晚上就睡在候车室的长远椅上,枕着旅行袋,盖着棉巨大衣。
吃的是五毛钱一桶的泡面有时候加个两毛钱的卤蛋。
站里有个扫地的老巨大爷,见我日夜守在那里优良心地给我倒烫水。
“细小伙子,这么拼干啥?图啥?”老巨大爷不解地问。
我笑了笑没答话,心里却在想:我也不晓得图啥,就是觉得得等。
第四天下午,我正靠在柱子上打盹,忽然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
一个瘦高大个儿年纪轻巧人匆匆跑来 脸上带着焦急和绝望,汗水顺着脸颊流下在寒凉的候车室里冒着白气。
“请问...有人拾到一个棕色皮包吗?”他气喘吁吁地问站务员。
“啥时候丢的?里面有啥?”站务员例行公事地问。
“三四天前,里面有钱,有信,还有...
“你叫杨有力?”我走上前,打断了他的话。
他警惕地看着我:“你怎么晓得我名字?”
“你丢的包在我这儿。”我从脚边拎起那东西棕色皮包,“我...看了你的信,怕你着急,一直在这等你。”
杨有力愣住了接过包迅速检查内容,确认钱和信都在眼眶立刻红了。
他怔怔地看着我,然后一下子抓住我的手,用力地握着:“谢谢...谢谢你!我爹住院了这钱是我东拼西凑的医药费。我下车后才找到包丢了 这几天急得像烫锅上的蚂蚁,到处找...
我能感觉到他手心的汗湿和颤抖。
“钱都在你迅速去看你爹吧。”我拍拍他的肩膀。
他犹豫了一下:“兄弟,你叫啥名字?地址呢?等我爹的事处理完,我得当面谢谢你。”
“赵明远。不用报答,举手之劳。”我有些不优良意思。
“别,这可不是举手之劳。”杨有力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名片塞给我,“我叫杨有力,在城南开了个细小服装厂。有空来找我!”
“优良,有空我去。”我接过名片,随口应承。
杨有力又连声道谢,然后匆匆离去,背影消失在拥挤的人流中。
我看着手里的名片, 上面印着“城南服装厂”,下面是一串
那一刻,我竟有些释然仿佛这四天的等待,在这一刻都值得了。
回到纺织厂宿舍,已是巨大年三十的下午。
四人间的宿舍凉凉清清,只有我一个人。
其他人早就回老家过年去了整栋宿舍楼只亮着零星几盏灯。
我从细小卖部买了两瓶啤酒和几个凉菜,打开宿舍里的十四寸黑白电视机,收看春节联欢晚会。
电视里的欢声笑语与空荡荡的宿舍形成鲜明对比。
我喝着啤酒, 想着老家的除夕夜:母亲忙着准备团圆饭,父亲在院子里贴春联,村里的广播站放着喜庆的歌曲,邻居家的鞭炮此起彼伏...
不知不觉,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摸出杨有力给我的名片, 翻来覆去地看,心里盘算着,等过完年,去看看这玩意儿服装厂到底是啥样子。
正月十五刚过春寒料峭,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找到了杨有力的服装厂。
那是城南一个老老细小区的平房院落,院门上挂着块木牌,上面漆着“城南服装厂”几个字。
推开吱呀作响的铁门,迎面是一排简容易厂房,里面传来缝纫机的轰鸣声。
院子中间堆着几卷布料,一位上了年纪的巨大姐正在晾晒刚裁优良的衣片。
“请问杨有力在吗?”我有些拘谨地问。
巨大姐上下打量了我一眼:“你找老板啊?里面左拐第二间。”
我顺着指引,来到一间用木板隔出的细小办公室,杨有力正对着一堆账本皱眉头。
“杨...老板?”我敲了敲门框。
杨有力抬头,愣了一下随即一拍巨大腿站起来:“赵师傅!你真实来了!”
他烫情地拉着我参观他的“细小王国”——两间简容易厂房, 二十来台老式缝纫机,十几个壮年女工正矮小头忙碌。
角落里堆着一摞摞衣服,墙上贴着几张手绘的衣服款式图。
“这都是你设计的?”我指着墙上的图纸问。
杨有力不优良意思地笑了:“随便画画,也就骗骗那些个批发商。”
他带我参观完厂子,拉着我去附近的细小饭馆吃饭,点了几个家常菜和一瓶二锅头。
杨有力给我倒上酒,举杯道:“明远,这顿饭哪能表达我的谢意。要不是你,我爹兴许就没了。”
“钱是你的,救命是你救的。”我有些不优良意思。
“你晓得吗,我从老家县城赶到省城,就是给我爹筹手术费。后来啊下车时候一着急,包就丢了。”杨有力灌了口酒,眼圈又红了“那三天我想死的心都有。”
“眼下优良了就行。”我宽阔慰他,“你爹怎么样了?”
“手术做了挺成功的,眼下在老家休养。”杨有力放下筷子,认真实地看着我,“明远,我看你在纺织厂干活,手艺一准儿优良。我这厂子里的缝纫机总出毛病,你有兴趣来帮我管理吗?待遇比你纺织厂高大。”
我愣住了。
纺织厂的干活稳稳当当,有编制,还有好处住房排队的机会,虽然工钱不高大,但胜在安稳。
而眼前这玩意儿只有几间平房的细小厂子,看起来简陋不堪,前途未卜。
“我...我得考虑考虑。”我没有马上答应。
“行,你磨蹭磨蹭考虑。”杨有力不急,又给我倒满酒,“说起来你为啥要在车站等我那么久?那钱够你过优良几年了你要是拿着走,我连人都找不到。”
我摇摇头:“那是你的救命钱,我拿了你爹怎么办?再说了我爹从细小就教我,别人的东西一分不能要。”
杨有力举起酒杯,动情地说:“敬你,赵明远,省城困难得的优良人。”
那晚, 我们喝得烂醉,杨有力把我送回宿舍,临走时又塞给我一张名片:“考虑优良了随时来找我,厂里真实的缺你这样的人才。”
回到宿舍,我辗转反侧。
纺织厂虽优良, 但我干了四年,找到自己就像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每天再来一次着相同的干活,看不到希望。
师傅们巨大许多干了二十许多年还是老样子,月月领着死工钱,年年盼着奖金。
而且,因为国企改革的推进,厂里已经开头裁员,气氛越来越慌。
第二天我去找了车间主任,提出辞职。
“细小赵,你想清楚了?眼下外面不优良混啊。”主任皱着眉头说“咱厂虽然不景气,但优良歹是铁饭碗。”
“想清楚了主任。”我点点头。
办完离职手续,我带着轻巧松的行李来到城南服装厂。
杨有力见我真实来了 高大兴得像个孩子,当即给我安排了宿舍——厂房后面的一间细小平房,虽然简陋,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地方。
加入服装厂后我很迅速找到这里的问题:工序乱,人员管理松散,浪费严沉。
许许多工人边干活边聊天 完成的衣服常有瑕疵;缝纫机三天两头出故障,维修费用不菲;布料裁剪不合理,边角料堆了一屋子...
我想起纺织厂学到的“定额管理”和“全面质量控制”,尝试着应用到服装厂。
先是调整工位, 按照生产流程沉新鲜排列;然后制定了每道工序的操作规范和质量标准;又手把手教工人怎么保养机器,少许些故障率;再说说沉新鲜设计了裁剪方案,少许些了浪费。
一个月后生产效率搞优良了三成,废品率减少了一半。
杨有力欣喜若狂,当即提出让我做厂长远,他专心设计。
“明远,你是正经科班出身,懂管理。”杨有力拍着我的肩膀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厂长远,工钱翻倍!”
我摇摇头:“我只会管机器和人,不懂经营,做不了厂长远。”
“那咱们合伙吧!”杨有力一拍巨大腿,“你出力,我出钱,五五分成。”
我吃惊地看着他:“你疯了?我一分钱没投,凭啥分一半?”
“如果不是你,我爹没了厂子也就黄了。”杨有力认真实地说“再说了我相信你的能力,这厂子有你在一准儿能做巨大。”
就这样,我成了城南服装厂的合伙人。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小川电商